【司想評論】【投稿】朱石炎教授:釋字七三七號解釋與偵查辯護

文/朱石炎(政治大學法學院榮譽教授、東吳大學法學院兼任客座教授)
司法院於民國(下同)105年4月29日公布釋字第737號解釋,對於偵查中羈押審查程序中應否及時使犯罪嫌疑人(註)及其辯護人獲知檢察官所憑理由與證據之爭議問題,提出肯定支持答案,具有重要意義。
刑事訴訟法(以下稱本法)往昔僅限於案件起訴繫屬法院後,被告或其親屬方能選聘辯護人。自71年8月修法以後,偵查中辯護制度始告建立,由於廣義「偵查」包含司法警察機關調查階段在內(見本法第二編第一章第一節體例),遂提前至調查階段即允許辯護人之參與,於是,偵查不公開原則,從絕對不公開變更為相對不公開。
鑑於被告是否被訴尚未可知,訴訟關係(對審架構)尚未形成,辯護人在偵查程序中,著重於提供法律輔助保障嫌犯權益,本法目前明定偵查中辯護人之權限,散見於§§34、34–1、101Ⅲ、101–1Ⅱ、103Ⅱ、103–1、107ⅡⅢ、110Ⅰ、245Ⅱ、255Ⅱ及263各該條文,有其侷限,難與審判中辯護人之角色相提並論。其中§34–1係於99年6月修正增訂,§245Ⅱ針對偵查中辯護人之在場權,最初(71年8月)僅規定「在場」二字,不過使其在場見證訊(詢)問程序之進行而已,迨89年9月修法以後,增列「並得陳述意見」六字,方具積極意義。
關於強制辯護,原僅適用於審判中之被告。95年5月修正§31,增訂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陳述之被告檢察官應指定律師為其辯護之規定,有限度擴及於偵查辯護亦可適用。嗣經102年1月及104年1月兩度再修正後,依照現行規定,
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陳述或具有原住民身分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在偵查中即有強制辯護之適用。上述情形與近鄰日本起訴前國選辯護比較,未來需否再擴大其適用範圍,尚有探討空間。(釋字第737號解釋理由書謂修法時允宜併予考量是否將強制辯護制度擴及於偵查中羈押審查程序一節,其見解雖值贊同,惟此部分非屬原因案件聲請範圍,似有訴外裁判及逾越權限分際之嫌。何況日本立法例仍有其限度,並未將國選辯護全面擴及於起訴前階段。)
首揭釋字第737號解釋,認為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應以適當方式及時使犯罪嫌疑人(註)及其辯護人獲知檢察官據以聲請羈押之理由暨有關證據,除有事實足認有滅證或串證等妨害偵查目的或危害他人生命身體之虞者外,不應予以限制或禁止,俾利有效行使防禦權。依本法現行規定,偵查中之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僅受告知羈押事由所據之事實,並未包括檢察官聲請羈押各項理由之具體內容及有關證據,與憲法所定剝奪人身自由應遵循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意旨不符,有關機關應於一年內修正本法妥為規定。上述解釋例,強化偵查中辯護功能及防禦權有效行使,對於偵查辯護制度之發展,深具意義。
至其所指「適當方式」,解釋理由書謂究採由辯護人檢閱卷證並抄錄或攝影之方式,或採法官提示、告知、交付閱覽相關卷證之方式,或採其他適當方式,事屬立法裁量範疇。
依余所見,如比照審判中案件採取全面開放閱覽卷證方式,在依本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理由聲請羈押之情形,存有嚴重後遺症,顯非可行,整體而言,基於達成偵查目的與維護嫌犯權益之均衡考量,以採取由法官於羈押審查庭向被告或其辯護人提示、告知或交付閱覽相關卷證之方式,較能靈活運用。
回顧法制演進,偵查程序逐漸淡化其糾問色彩,已是時勢所趨。偵查機關雖須從事起訴前之準備工作,而被告亦有為自己預作防禦之必要,此在羈押審查程序階段尤其重要。釋字第737號解釋對於及時獲知卷證資訊事項予以肯定支持,至為正確,頗值讚揚。偵查辯護制度之建立與強化,其目的非為掣肘辦案,羈押屬於最嚴厲、最嚴重之強制處分,至盼檢察同仁提出聲押時,務求蒐證齊全,以重人權。
(註)本法對於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涉嫌犯罪之人,稱為「犯罪嫌疑人」,案移檢察官偵查中,即稱其為「被告」,釋字第392號解釋亦以偵查中之羈押「被 告」相稱,並無不妥。此次第737號解釋基於無罪推定原則及憲法第8條意旨,在解釋文及理由書中,對於檢察官偵查案件聲請法官羈押「被告」改稱「犯罪嫌疑人」,顯與法律條文不符。偵查階段可否使用「被告」稱呼,確實值得探討,但在未經修法以前,不應隨意變更用語。何況憲法第8條本身並無「犯罪嫌疑人」一詞,且其所指「犯罪嫌疑」者,係從廣義,包含案件確定前之被告在內,是則對照本法第154條第1項所定無罪推定原則文句,豈非對於審判中之「被告」亦應改稱為「犯罪嫌疑人」?本文認為第737號解釋此項變更用語尚欠妥適。
評論專區
精選影片

星宇涉年齡就業歧視遭罰30萬|不給面試機會就是歧視?雇主如何避免踩到年齡就業歧視罰則?

川普關稅戰震驚全球|打破現有體制?劃分敵我陣營?川普到底在盤算什麼?

高院庭長縱放鍾文智潛逃?合議庭都是假的?需要深究法官可能成立的刑事責任!

賴總統提恢復軍審制度|不應走回頭路!恢復軍審制度後,最大的問題會是什麼?

台積電赴美投資|護國神山垮了?台灣被掏空?半導體產業就此一片漆黑?

川普、澤倫斯基撕破臉|川普有什麼打算?趁火打劫?美國會放棄烏克蘭嗎?

北市佛教精舍命案|宗教團體該受管理嗎?該怎麼管?

路邊卸貨害死人|經營者應檢討,別再把經營成本外部化!

郭董欠12億獎金挨告?簽的是什麼合約有影響嗎?戴正吳為什麼選擇以勞動事件提告?

台版「地面師」詐欺案|詐團盯上獨居長者!有什麼防堵的好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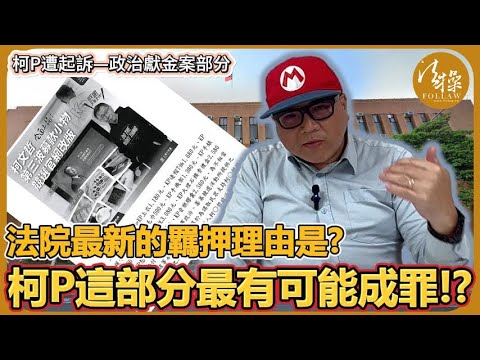
柯P遭起訴——政治獻金部分|法院最新的羈押理由是?柯P這部分最有可能成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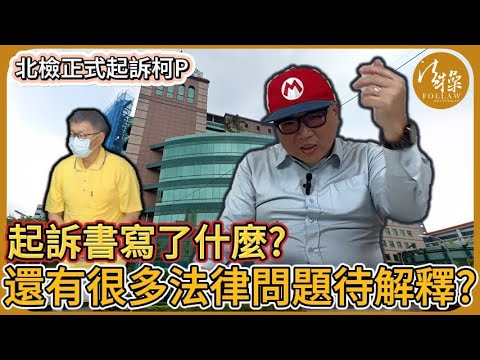








 LINE
LINE